1977 · 那年高考|五位复旦教授因1977改变人生:幸运赶上转折点
40年前,无数渴求知识的青年人在隐约的希望中编织着美好的梦想。1977年,中国恢复了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。这一消息将青年们从迷惘与困惑中拉了出来,让他们看清了前方的道路,找到了努力的目标,拥有了实现理想的可能。此后,千千万万青年通过高考走向了另一种人生。今天,就让我们听复旦管院的芮明杰、徐以汎、薛求知、郁义鸿、张新生等5位教授聊一聊他们的1977和那段激情岁月中的故事。
忆往昔,岁月峥嵘

本文图均为 微信公众号:复旦管院 图
芮眀杰 教授
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系主任
1977年参加高考,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
在大城市生活惯的人初下农村还真不习惯。我倒是还很快适应了,前后一共待了六年之久。
天晓得,那时候的我们算来算去也还是小学水平。其实说起知识,我也没有什么。就是小时候杂七杂八读过些小说和科学普及方面的书,因为小时候的梦想老是在科学家与作家两个方面摇摆。
我当时一心想上中文系,没想到听了我的作家梦,全家人都投了反对票!他们还是反复强调那句老话: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!

芮明杰教授在插队时所住的小屋前留影。
高考当天,我早早起床,骑了四五十分钟的自行车赶到镇上的考场参加考试,中午就到小镇上买碗面条作为中饭。语文、数学、政治和理化考了整整两天。
放榜时,我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,非常紧张,快五点了也没有消息,我怕是真的没戏了。后来,我去田的那一边挑粪,听到一个农民远远地喊我“芮博士,你的通知书来了!”我心头大喜,扔下粪桶就冲了过去。
因为多年的耽误,学校不得不花半个学期给大家补习初等数学,然后再进行数学专业的专业课学习。这也可见学校对77级学生的重视。那时候我们学习都很用功,每天都是等到整个教学楼要熄灯了才回宿舍,真的很辛苦。

芮明杰教授大学同寝室的七位同学。
大学要毕业了,当时教育局不让我们考研,希望我们留下来成为学校的骨干,一直到开始报名的第二天才允许开介绍信报名,我当时选的专业是工业经济。
其实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只觉得这个专业可能有些长处可以发挥。数学王国太完美,在其中若想做出一点事情,很难;然而经济管理在我们国家还很空白,肯定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,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专业。
小平同志在1977年的新思想和新政策改变了我们的人生,让我们不仅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,更有机会在社会上做出一些成绩,成为更加有用的人。
环境造就人生

徐以汎
徐以汎 教授
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系主任
1977年参加高考,考入山东矿业学院数学班
当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,初高中4年总共发了6本书——两本数学,两本物理,一本化学,一本生物植物。高考前,翻出这些书,才发现都是新的。只有第一本数学书边缘有点黑。 其他时间就是要么农忙的时候就去某个农村大队割麦子、要么就是去哪个工厂劳动,几乎没有正正经经地读过书。
其中有运气的因素,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学什么专业好,先考入山东医学院,有书念就很满足了,考虑不到自己的兴趣,也没啥概念,考上了就好。后来,转入山东矿业学院。

徐以汎教授年轻时。
那个时候,学习机会来之不易,大家都很珍惜。当时我们每个班都有一个固定的教室,固定的位置。老师每天到教室来上课。不论周日与否,教室里不到晚上十点总会有人在学习。这和学生自己的要求也有很大关系,毕竟隔了那么多年,大家都有一种上进的责任心。最重要的一点,这是自己的选择,不是别人逼你做的。
要继续深造了,中科院是我一直很向往的地方。中科院的学生都很厉害的,那时候,通宵不睡是家常便饭的事情。有时候晚上我坐在窗前工作,坐着坐着,天就亮了!那种感觉很美好,真的!
高考给了我自由选择的权利

薛求知
薛求知 教授
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
1977年参加高考,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
从名义上讲,我是68届的初中生,正儿八经的中学教育只接受了一年,遇到“文革”就停了课,后来断断续续上了点“革命”课,所以连初中毕业也是打折扣的。
我只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,记得那时大家用的都是手抄的资料,用复写纸,一抄就是好几份,分给不同的人复习。我和同事都是白天上班、晚上复习,而且我们之间常常会搞些小竞赛,看谁记得准、想得妙,这样复习起来还挺有趣的。

薛求知教授年轻时的照片。
那一年参加高考的人达到570万,录取比例不足5%,竞争非常激烈;虽然考试难度不大,但时间太紧,资料缺乏,大家都没法好好准备,靠的就是原有的底子和现场发挥能力了。
我记得作文题目是《伟大的胜利——难忘的1976年10月》,我找了一种独特的文体,以给朋友的一封信的形式来组织整篇作文。(凭借这样出新出巧的构思,薛老师获得了整个考区作文的最高分。)
我们那时不仅有一流的老师,也有积极勤奋的学生。大家学习都很刻苦,经常在晚上熄灯以后跑到走廊路灯下看书,早晨五点多钟就在林间小路背诵英语单词。我们如获至宝地收集着老师的授课内容,在课堂上卖力地记笔记。我也练出了一门功夫,基本上可以一字不漏记下老师每节课上的话,而且字迹整洁。有好些下一届的学生都拿我的笔记作考研参考呢!

1977年高考之前,薛求知教授在延边财贸干部学校学习并留校任教。
高考的恢复,首先恢复的是知识本身的尊严和地位,十年内大学教育的中断和畸形运转,本身就是对知识的亵渎;而高考作为一种正本清源,回归了全社会对知识追求的热情。
在更深的层面,我认为高考重新赋予了中国青年自由选择的权利。在此之前,每个人读书的权利都是由别人来决定;在此之后,所有人都可以考大学、可以填报任何一所大学和专业,这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恢复。
没有转折的人生不算精彩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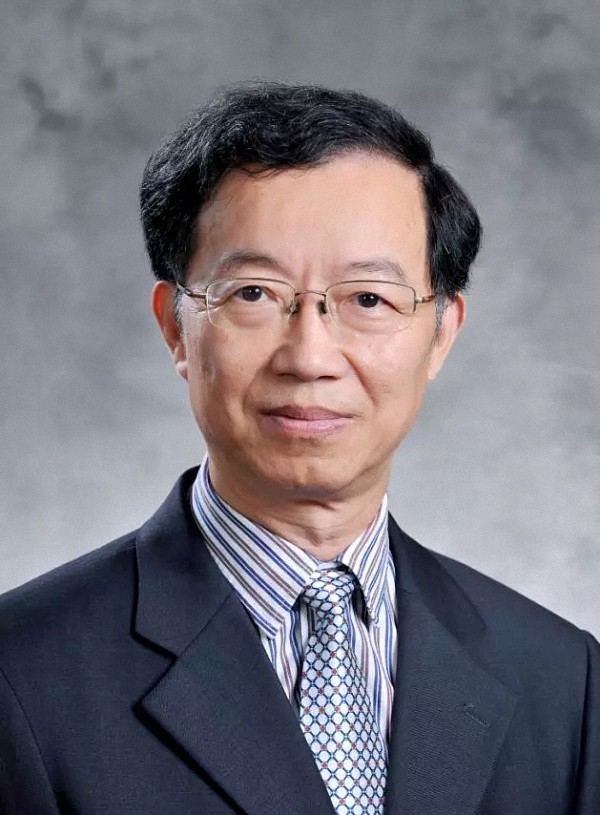
郁义鸿
郁义鸿 教授
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
1977年参加高考,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
拾级而上的初等教育在1966年戛然而止。1969年3月,我随着知青大流去到黑龙江国营农场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。遍尝各种农活的辛劳而得到体魄的锻炼之余,我们也有机会读到好多世界经典名著,很多课堂之外的知识都是在那个时候获得的,却也荒废了正规的学科教育。
本来我在1973年就有机会进大学学习。当年也举办了入学考试,我三门课程全A,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老师还给我做了面试。后来变成推荐上学,我一个书呆子,从来不善交际,推荐上学自然与我无缘,于是乎就不得不在富饶的北大荒继续我“修地球”的生涯。

郁义鸿教授年轻时在天安门广场留影。
复习迎考的热情可想而知。连队“战友”大多来自上海的一些重点中学,于是从各种渠道搜集来复习资料。像我这样只读了一年初中课程的半文盲,在复习交流中得到的那些高中学长的帮助难以细数。然而,最终能够报考复旦并被录取,不能不说有着命运之神的眷顾。
本科数学四年,让我从中获益一辈子的是思维的逻辑性。当年选择专业颇受陈景润的影响,但也确实对文理工医等等学科分类不甚了了。毕业时改行到刚刚组建不久的管理科学系读硕士,读的是数量经济方向,并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经济学。毕业留校后,择机在职读了博士。

郁义鸿教授年轻时。
如果没有恢复高考,我会在哪里?我不知道。最大的可能是继续“修地球”,也或许享受后来的政策顶替父母的岗位或病退返城,或许进当地的工厂做工……太多的或许,因为个人的命运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决定的。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,就是无论是否进大学,我会一如既往地读书,我就是个读书人,一个书呆子。
我相信,循着大势去看,高考的恢复只是时间问题。我们幸而赶上了。
不读书就没知识。要说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,不如说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不仅是对人类,对一个民族和个人,又何尝不是如此?
大学是最宝贵的读书时光

张新生
张新生 教授
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统计学系系主任
1977年参加高考,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
对于当年高考,我印象最深的是,最后一门考物理和化学,走出考场后一片哗然,大家都在叫嚷,物理和化学的试卷太难了!事实也确如此,这份试卷满分100分,大家的平均得分只有40分左右。
我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,当得知自己考取安徽师范大学时,那种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。

张新生教授年轻时在安徽师范大学。
我就读的数学系,大约有近两百个学生,我是当中年龄最小的之一。当时有一件事让我今生难忘:入学第一次考解析几何,我只考了三十几分,但有的“老三届”的同学甚至考满分。这也促使我从一入学就更加努力地学习,圆满地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。
当时生活条件很差,十个人住一间宿舍,十一点就会熄灯,但是大家学习都很刻苦。每一个同学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,全部精力都在课业上,即便是这样都觉得看书时间不够,很少会想什么娱乐活动。
每一堂课后,我都会在课下花三倍以上的时间复习巩固。辅导员经常劝学生不要看书太晚,但绝大多数同学都不会在教室十点钟熄灯之前离开。

安徽师大77级“随机过程”学习班师生留影。
大学四年是我学习知识最为密集的时期。最初我对数学并不是很感兴趣,但不断深入后,兴趣却越来越浓厚。
我们使用的教材是国内知名版本,例如《概率论》和《实变函数》就都选用复旦大学编写的教材。
大学四年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,在大学里,你将学到思考问题的方法,领悟对世界的认识,真正形成自己的世界观。能否珍惜和利用这四年,对于一个人长远的人生规划至关重要。
(原题为:《1977,教授们的高考故事》)
来源:复旦管院
转自:澎湃新闻